弟兄各分東西
西元1054年7月的某日,在君士坦丁堡(現稱「伊斯坦堡」Istanbul)聖索菲亞大教堂(Sancta Sophia)一幕戲劇化的場景,關鍵性地決定了「希臘東方正教」(Greek Orthodox Church,包含希臘、俄羅斯和其它屬於此系統的教會)和「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即今日通稱的「天主教」)的分裂,從此各分東西。前來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塞路拉利烏(Michael Cerularius)談判解決宗教上爭議的羅馬利奧九世(Pope Leo IX)教宗特命代表洪伯特樞機主教(Cardinal Humbert),在眾人一片驚愕中,盛裝登上教堂的祭台(altar),宣讀教宗諭旨,將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塞宗主教、及其從眾全數開除教籍(excommunication,此舉在宗教意義上「茲事體大」──不得領受教會聖事,即代表不能獲得來世永生的救贖;現世眾人也當唾棄他),隨後,抖落腳上的灰塵,揚長而去,返回羅馬。當然,塞宗主教也不甘示弱,宣佈將利奧教宗和他的代表們「開除教籍」,並聲言整個西方的拉丁教會都是「異端者」(heretics)。
細究自從第四世紀以來的東西羅馬帝國之間,在地理阻隔、語言和文化差異、政治上迥然不同的大環境、宗教事務和生活的取向方面,東西雙方教會的來往和溝通不良,鴻溝日益擴大,齟齬從來不斷。
西元330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遷都於東方的君士坦丁堡,一則為了東方廣大而富庶的領土,另則為遠離日益入侵北方邊界的各蠻族。而395年後,東西羅馬各自選立皇帝,更確立了迥異的雙方──說希臘語的東方和說拉丁語的西方。拉丁人的「務實」特性表現在宗教上的法律、組織、和責任方面。希臘人的窮理思考和捷辯,導致多次重大的、各不相讓的、長期的神學爭議。
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和綿延數百年的蠻族入侵等,造成西歐的破碎。眾多獨立的小地區或無政府狀態,促使已然組織架構完備的天主教會參予一般的民事行政,蔚為社會上的主導力量和機制。第八世紀末,教宗和法蘭克王國(Franks)的結盟關係,除獲得了實質的保護之外,也樹立在俗世社會中的權威。主導傳教版圖的擴大,遍及西歐,並積極參予各地的教會事務,羅馬城的主教(即,教宗)不僅是全教會的首席(primacy),而且也是全體教會的「管理者」。
拜占庭(東羅馬)皇帝歷來施行「君權指導教務」(Ceasaro-Papism)的政策,雖視教會事務為己任,但多參雜政治上的考量,教會本身也因而不能堅持純宗教上的立場。既然不能提供拉丁教會實質的保護,也就喪失了主導拉丁教會事務的發言權。在加洛林王國(尤其,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間)時期,拉丁教會雖歷經類似的「君權主導」(Theocracy)政策,但為時短暫。政治上長期多頭分立的局面,促成羅馬教宗獨大的角色,是整個「基督王國」(Christendom)的領袖。
第四世紀之前,天主教會的重心在東方──耶路撒冷、安提約基亞、亞歷山大里亞宗主教區,涵蓋了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羅馬宗主教區的教會人口甚至於比不上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教區。然而,此時教會的重心已然西移。七世紀興起的回教(Islam)在不到一百年內迅即席捲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以及大部份的西班牙。羅馬教宗強調是全體教會首席的地位,而在領袖西歐之餘,更思涵括東方教會,必然地會和拜占庭皇帝主導的東方教會有所利益衝突。何況,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俄羅斯(Russia)和其它斯拉夫人地區於第十世紀末之前陸續歸屬它的轄區後,豈肯屈就?
東、西雙方的教會,在語言(希臘正教使用希臘語,而且准許斯拉夫語等地方語言的使用;羅馬天主教堅持統一的「拉丁語」,以迄於1960年代)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再加上地理的阻隔,表現在宗教的日常實踐上,日見差距。
第八、九世紀,在東方教會中反覆成為重大爭執的「聖像毀壞者」(Iconoclasts)事件,在西方教會中從未造成困擾。
在第四、五、六世紀的重大神學爭議事件結束後,東方的希臘教會日漸重視各式的禮儀,視之為具有屬神的奧秘(mystery)或神力──「宗教信仰在行動中」(Faith in action),亦即,正在實踐所相信的教理──它們乃是具有賞賜神恩的「聖事」(sacraments)。由於較少強調倫理、道德方面的佈道,以及其在日常生活上實踐的重要性,於是,造成神學上的停滯現象。這個觀念和傳統,也適時地傳遞給了新近接受基督信仰的各個斯拉夫民族的地區。
拉丁教會也有「彌撒」[[Mass,包含,重行「最後晚餐」的聖體聖事(Eucharist)]和七件「聖事」(sacraments),同樣強調屬神的奧秘和神力。但對各式的教會禮儀和細節,視之為外在表現的一種形式──因此,是可以隨著需要而改變的。
「教士獨身」(clerical celibacy)、守齋(fasting)、無酵餅(unleavened bread)使用於聖體聖事(即外界通稱的「聖餐禮」)和聖神(Holy Spirit)是由聖父及「聖子所共發的」(Filioque)等,就是1054年7月君士坦丁堡會談中,東、西雙方教會在宗教爭議上的焦點。雙方在認知觀念上的差距,是不能溝通的原因之一。
希臘人自視為典雅文化上國,固然一向鄙夷「番邦」(即,當時的西歐)的來人。然而,家道中衰的世家子弟,橫遭篡奪家產(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並在此立國達57年之久)的奇恥大辱,是雙方終究無法復合的致命性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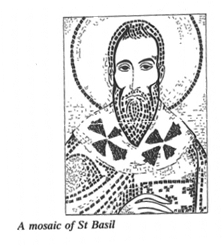
辭彙(註解)
※ 羅馬皇帝參予(或干涉)教會有關教理的爭議(即,Ceasaro-Papism)的重大事例及其影響──
亞略異端(Arianism)
西元313年任職埃及亞歷山大(Alexandria)某教堂的亞略(Arius)神父倡導這個道理:宇宙唯一真神的天主從無中創造了「聖言」(Holy Word)(即,後來降生人世的耶穌),並收他為義子。(編者註:由於這個神學上的爭議,後來也因而確認了天主「三位一體」Trinity的教理)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剛統一了羅馬帝國,發現整個東方(希臘)教會地區已被這個爭論所分裂(編者註:313年的米蘭詔書承認天主教為合法的宗教)。首先,乃 出於對帝國和平的關心,皇帝出面召開全體教會主教參加的大公會議,希冀獲得一致的結論以平息此爭議。325年,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城(Nicaea)舉行的大公會議(天主 教會首次的大公會議),共有318位主教參加。大會議決了一個簡明而條列式的教理信條,亦即「尼西亞信經」(Nicaean Creed,迄今仍被教會奉為信條,雖後世略有增添),以供全體教會奉行不渝。然而,此事件並未就此了結。許多簽署的主教仍是亞略異端的擁護者,只因懾於皇帝的臨在於當場及其權威。君士坦丁死後繼位的公斯坦二世和瓦倫斯皇帝都是亞略的服膺者,他們驅逐正統派的主教,代之以亞略派者。這個爭議數十年後方才平息而定於一。
聶斯托里教派(Nestorianism)
第五世紀的君士坦丁堡總主教聶斯托里(Nestorius)想要調和「耶穌是生於瑪利亞、生活並死在巴勒斯坦」而又是「天主真神」(即,三位一體)的道理,因而宣稱,耶穌不只是具有兩個性體(即,天主性和人性),而且還有兩位。
論戰又起,皇帝又出面調停。431年在小亞細亞的厄弗所城(Ephesus)召開的大公會議,議決:「耶穌雖兼有人性和天主性,但只有一位(person),亦即,天主『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因此,譴責了這個異端。直到433年,正反雙方才正式和解。
然而,餘波未平。大致上,是敘利亞地區支持聶斯托里學說。489年,在皇帝下令關閉他們大本營的厄得薩(Edessa)神學院後,在波斯另創了一個神學院。這個地區的支持者往外傳教,遠至阿拉伯、印度、蒙古、和中國〔唐朝時到達長安的教士阿羅本(635A.D.,貞觀九年)即隸屬這個教派〕。
一性論(Monophysitism)
這個爭論延綿最久,影響也更大。歐廸克(Eutyches)是君士坦丁堡一所修道院的院長,聲稱耶穌的「人性」在其生活成長的過程中,被他的「神性」所吸收了,亦即是「一性論」。
君士坦丁堡總主教弗拉維(Flavian)召集本地區的32位主教開會,在質詢歐迪克的答辯後,議決此乃謬說。但444年擔任亞歷山大里亞總主教的戴奧斯科(Dioscorus) 聲援歐廸克,而皇帝狄奧多修二世也保護他。因而有449年的厄弗所大公會議,由戴奧斯科總主教主持。罔顧羅馬教宗利奧一世(Pope Leo I)大部頭式長篇濶論的指示,大會平反了歐廸克,皇帝批准大會決議文,並威脅膽敢抗議反對的主教們。
450年新皇帝即位,大環境丕變,歐迪克遭下獄,先前被驅逐的抗議主教們皆平反。利奧教宗同意皇帝於450年在加采東(Chalcedon,與君士坦丁堡隔著博斯普魯斯海峽)召開的大公會議──共630位主教參加,幾乎全數來自東方的希臘教會,僅5位來自羅馬教宗的代表,是迄1870年為止,規模最大的全體教會層級的主教會議。為期三週的加采東大公會議,議決了一個「信仰宣示」──我們宣示,一個而且相同的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具有兩個性體(natures),彼此未曾混合、轉化、分割、或分離……每一個性體的各個特質都維護及生存在同一個位格(person)。
僅就神學上的問題而言,加采東大公會議已決定性地一次解決了。然而,各地一性論支持者的態度又是另一回事。急思脫離羅馬帝國的敘利亞和埃及地區,地方上民族反抗的情緒,適時地援引了神學異議的外衣。埃及的一性論擁護者,開始使用本地的「考布地」(Coptic)語言在教會的日常禮儀,而捨棄傳統的希臘語(Greek)。分裂的埃及教會(迄今仍佔埃及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和衣索匹亞(Ethiopia)教會(今日,佔該國總人口的60%,是為國教),因而被稱為「考布地教會」(Coptic Church)。同樣地,敘利亞語(Syriac)成了敘利亞一性論者的禮儀用語,被稱為「雅各教會」(Jacobite Church,因六世紀領銜的厄得薩主教Jacob Bardaeus而得名)。高加索山區的亞美尼亞(Armenia)亦然。
往後的230年期間,在贊成、反對「一性論」和舉棋不定的東羅馬帝國皇帝的不同措施聲中,這個爭論在教會中或大或小地延燒著。
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即帝位後,尋求與西方拉丁教會的和解。680年11月至681年9月召開的第三屆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專為解決「一性論」的爭議,全教會的五個宗主教(patriarches),或親自或派代表,全程參加。再次確認了加采東大公會議的宣言。
皇帝的合作,當然也有大環境的考量。一性論者的大本營──埃及和敘利亞──現已全被回教勢力所征服,不再有所指望了。而先前查士丁尼皇帝收復的義大利半島,自從568年倫巴底蠻族(Lombards)人侵義北後,威脅日深。值此帝國勢力不張之時,皇帝急需羅馬教宗的支持,以穩定義大利的領土。
※「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344–407A.D.)──
這是一個東羅馬皇帝,在「皇權高於教權」(Caesaro-Papism)的政策下,干預和影響教會事務運作的例子。
約西元344年出生於安提約基亞(Antioch,今敘利亞境內)的聖人金口若望(因其博學、修辭和雄辯技能、嫻習聖經及修道的德行、講道時鏗鏘有力,能吸引眾人來聽講,故得「金口」其名),於397年被皇帝阿卡廸斯(Arcadius)選任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忠於職守的若望宗主教,敢於批評皇帝宮廷內腐敗的人和事,尤其對皇后的失德不假辭令,樹敵眾多。
妒嫉金口若望的埃及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總主教得奧菲路(Theo- philus),在皇帝的支持下,於403年召開一個有35位主教(bishops)參加的「跨教區聯合會議」(synod)審查若望的宗教言論。因參與的主教人選多為得奧菲路所挑選,會議結論判定若望所傳乃是「異端」(heresy),並將他放逐。
一年後,屈服於君士坦丁堡眾信友的要求,金口若望被召回,重任宗主教。但因他堅持指摘皇后的失德言行,於404年再度被驅逐。三年後,他在困苦的流放中逝世。直到三十年後,他的遺體才被隆重地迎回君士坦丁堡埋葬。
※聖像毀壞者(Iconoclasts)──
「Icon」是指有關於「天主」(God)、耶穌(Jesus)、聖瑪利亞(Mary,耶穌的母親)、和諸聖者的圖像(image)。Iconoclasts即是image-breakers(圖像的毀壞者)。這個爭論,乃是一種儀式的問題,基本上不涉及神學上的爭議。但是,在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皇權主導教會」的政策下,皇帝個人的好惡多次顛覆了東方希臘教會的傳統,也損及它與西方羅馬教會系統的關係。
初期的天主教會,謹守猶太人的傳統,惟恐異教徒崇拜「偶像」(idolatry)的習俗。直至被立為羅馬國教後,畏懼感漸消。到第七世紀時,為教導聖經故事,以及引觸祈禱的氛圍,圖像、馬賽克瓷磚畫和雕塑像廣泛地在教會內使用,蔚為傳統。
質樸的宗教虔誠者,當然也能援引舊約聖經,遽爾論斷它為「偶像崇拜」。東羅馬皇帝利奧三世(Pope Leo III)是一位「聖像毀壞者」,他在726年諭令摧毀帝國境內的各類宗教圖像,也得到主教會議的追認。由於教會內的反對聲浪,繼任皇帝又指示主教會議平反之(787年)。在第九世紀時,舊事又重演。礙於反對聲浪,皇后狄奧朵拉(Empress Theodora)出面干預,於842年指派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並於次年召集跨教區主教會議,再度恢復對於聖像的敬禮(veneration of images)習俗。
在此東方教會長期的、反覆的「聖像毀壞者」期間,西方拉丁教會始終維繫敬禮聖像的傳統,但也因而產生對東方教會的反感。
※東(希臘)西(拉丁)方教會數次的分裂與僵局──
東、西羅馬帝國的歷史上與地理上分立的事實,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以地域性管轄(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的主教區為基礎的區域性的分立,乃至於誤會無法溝通的分裂。茲略述歷史上數次由小至大的東、西雙方教會的分裂。
「阿卡西烏的分裂」(Acacian Schism)──
在牽動全體教會關於「一性論」(Monophysitism)神學爭議的歷史過程中,451年的加采東大公會議雖已在神學討論上議決了這個爭議,但在各類因素的組合下,仍餘波盪漾。真諾皇帝(Zeno)為平息爭議以求帝國境內的和平,於482年採行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阿卡西烏(Acacius)提出的折衷方案。但遭教宗菲利(Pope Felix)的極力反對,並重申利奧教宗在加采東大會上的名言──「(耶穌的大弟子)伯多祿透過利奧在此發言」──強調羅馬教宗在全體教會中的首席地位(primacy),並進而罷黜阿卡西烏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職位,以及譴責皇帝。因而,造成了為期約35年的東、西雙方教會的分裂。
西元518年,繼任的尤斯定皇帝(Justin)與羅馬教宗何米思達(Pope Hormisdas)重開談判。所謂的「何氏條款」(Formula of Hormisdas)被東方教會的主教們所接受,並認知(acknowledge)羅馬教宗在教會事務爭執事件中的指導權,因而雙方和解。
波提烏的分裂(Photian Schism)──
這次東、西雙方教會的分裂,發生在君士坦丁堡宗主教(patriarch)波提烏(Photius)的任上(857–867;877–886),完全導因於人為的因素。
波提烏乃是一位俗世人(layman,亦即,非經祝聖過的神職人員),也是頗負盛名的學者。他的前任聖依納爵(St. Ignatius)因直言批評皇帝的寵臣巴達斯(Bardas)且拒絕他領受聖體(Holy Communion,編者註:這是何等的大事啊!因為,拒絕他領受這個「聖事」關乎巴達斯的來世救贖,況且,也等同昭告帝國人民棄絕他。)而遭罷黜。但是,羅馬教宗尼可拉斯一世(Pope Nicholas I)拒絕認可波提烏的任命,除非前後任的兩人均來羅馬當場評理。
皇帝魯莽地拒絕羅馬教宗的首席權,而波提烏更以宗主教通函公告東羅馬各教區周知的方式,詆毀教宗的要求,並責斥拉丁教會為異端者(heretics)。教宗將皇帝和波提烏均開除教籍(excommunicated),而希臘教會的主教會議則報復以開除教尼可拉斯一世的教籍,雙方正式鬧翻了。
篡位的新皇帝巴西爾(Basil)清除舊勢力(包括,波提烏去職),重新和羅馬教宗和解,868–870年的大公會議,重又確認教宗的首席權。七年後,巴西爾皇帝改弦易轍,再任命波提烏為宗主教。波提烏於879年主導另一個大公會議,成功地為自己平反。時任羅馬教宗的若望八世(John VIII)試圖處理此事,但他旋遭謀害,而隨後羅馬的動亂也不了了之地暫時平息彼此的爭執。但史家認為,雙方的分裂,事實上已經發生了。
至於波提烏,新皇帝利奧六世(Leo VI)上任後,即迫不及待地以自家的兄弟史蒂芬(Stephen)取代了他。
※歷史背景與地理阻隔的舉例說明──
西元330年,君士坦丁皇帝將羅馬帝國的首都,由羅馬城遷至東方的君士坦丁堡。
西元395年,狄奧多修皇帝(Theodosius)再度諭令東、西羅馬帝國的分立,並以羅馬城為西羅馬帝國的首都,分別選出自己的皇帝。此舉乃是反映東、西羅馬雙方既存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巨大差異。
西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國滅亡。但淪陷的消息,40天之後才傳到羅馬教宗。可見雙方地理上阻隔的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