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組
前言
這期封面故事〈使命翻轉〉,顧名思義是福傳「使命」可以、也需要因應地方而「翻轉」,從另一角度及思考模式來省思耶穌所指的「重生」與「遇見天國」。
印度神學家雅瑪拉神父綜合了五個「典範轉移」挑戰身為亞洲基督徒的我們,勇敢走出我們的舒適區,在這多元背景的亞洲社會裡,與他人互相學習,進一步相知、相惜、相結合,豐富彼此的信仰生命。
從中國到西伯利亞、從外蒙古到印度尼西亞、從日本到印度,在亞洲這充滿多元文化、多種語言、多元民族的豐富土地,有說不完的故事。以基督為中心的信仰,不管是在西方或在東方,都有聖神在工作,祂在每一個獨特的民族、文化、語言中運行,並展現多樣及別緻的風貌與魅力。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諭中,清晰的闡述「福傳使命」的狹義定義是:(1)「宣講」基督的福音;(2)建立團體,使「天國」活潑的形象臨在和活動於人間(RM19)。
因此,福傳的使命,不應只停留在「宣講天國」,而是實踐並活出「福音的價值」。教會的存在主要就是為「基督的福音」服務,因此之故,教會應致力推動「和平、公義、友愛、關懷貧窮」,以實踐天國臨現於人間。請看這一期的封面故事:〈使命翻轉〉。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傳使命的新面貌
前言
印度籍耶穌會士雅瑪拉神父(Michael Amaladoss SJ),目前是印度「文化及宗教交談機構」(Institute for Dialogue with Cultures and Religions, Chennai, India)總監,也是當今印度及亞洲頗有份量的重要神學家。
雅瑪拉神父在印度南部的天主教家庭長大,於1953年加入耶穌會。他除了接受耶穌會的正規陶成教育外,也曾研究南印度古典音樂、藝術和文化。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關於「聖事禮儀中可變與不可變的元素」。他從巴黎天主教學院(Institut Catholique in Paris)學成後回到印度,創立了宗教交談小組,也在新德里耶穌會神學院任教。
他也曾擔任耶穌會前總會長柯文伯神父(Peter-Hans Kolvenbach)12年的特別顧問。據說他不喜歡被稱為教會神學家,而更希望被稱為「對福傳與對話、教會本地化、及解放神學有興趣的神學工作者」。[1]
談到「宗教交談」,雅瑪拉神父認為,宗教交談不僅僅限於宗教領袖、也不僅止於學術範疇,宗教交談需要信徒和社會百姓之參與。
雅瑪拉神父說,他服務的機構設有不同的小組,與各個宗教展開對話,並研究宗教群體間的暴力衝突,從而尋找和平出路。他說,該機構會為學校舉辦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認識其他的宗教,以瞭解宗教交談的重要。「共同祈禱可以是交流的第一步,每位教徒的祈禱經驗都是寶貴的。第二步可認識其他宗教的教導、經典、聖人和代表。」[2]
雅瑪拉神父在本文清楚指出及證明東方(亞洲)人的圓融與多元思維如何詮釋「梵二」後的教會觀。他以東方人的思維模式,綜合出教會觀的五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引領我們以另一角度及概念來瞭解教會。新的觀念將使福傳使命的面貌獲得新的詮釋。
他提到的五個「典範轉移」包括:
1. 從教會至天國
2. 從福傳使命至對話
3. 從支配操縱到服務
4. 從出世(神聖)到入世(世俗)
5. 從統一到和諧
如果說這五個典範轉移為五個新圖像,希望讀者透過這次的專題內容,可以試著把這五個圖像存留心中,時時「拿出來細細品味及觀賞」,適時讓它展示在我們的福傳任務中!

------------------------------------------------------
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給我們做了個適應本地文化的示範,他穿著歐洲貴族的服裝在比睿山尋求與高僧對話,因為他認為這些僧侶與印度南部海岸的貧困漁民相較下更有學識。這種適應本地人文環境的福傳方式、早在利瑪竇(Mateo Ricci)和羅伯特(Roberto de Nobili)時代,就已在亞洲地區扎下了根。
適應本地文化精神的福傳理念,一直都不斷在進行及延續中,天主教和其他文化、宗教之間的相遇與交流,尤其在上個世紀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已經歷過許多的典範轉移/概念轉變(paradigm shift)。普世教會以及亞洲教會都見證了這些福傳原型之轉變。因此,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這福傳的歷程,不僅如此,也邀請諸位一起抱持夢想、理想、及計劃未來的心態,來回顧這些改變。

本文針對五項福傳使命的典範轉移做回顧及反思。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不擬對神學背景多所探討,但會針對個別的典範轉變提出關鍵性的反思。
1. 從教會至天國(From the Church to the Kingdom of God)
過去教會的最終任務即是「培植教會」(planting of the church),但往往只是「移植」歐洲的教會,包括她的結構、教義和禮儀。儘管傳教士本身可能已經努力適應當地的文化和背景,然而他們並沒有使教會真正適應當地的文化。即使有,也僅止於一些局部的、調適性的整合。
今天我們意識到傳教使命的目標具有雙重幅度:教會是「建立神的國度」,同時「教會把自己視為此國度的標記及僕人」。
福傳使命是繼承天主的使命,亦是首當其衝的任務。這位天主是那賜予聖言及聖神,願意與人類和世界分享生命,並願意「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祂(弗一10)的天主;祂是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十五28)聖言及聖神存在並且活躍於普世各民族、各文化及各宗教中。天主聖言在耶穌身上降生成人、為了讓普世的「和好與共融」計畫得以推進。
天國是「已經」及「尚未」的動態現實。關於這一點,印度耶穌會士聖經學家索爾斯─普布(George Soares-Prabhu)說:
「當天主愛(王國)的啟示與人對此愛的信任與接納(懺悔)相遇時,一個強而有力的個人與社會之解放運動就此產生,並貫徹人類歷史。此解放運動會帶來自由,因為它釋放了每一個人的執著與不足、促進人類的團結,且賦予每個人行使這份愛的自由、彼此真誠地關懷。此關懷將帶領人類通往正義,促使每一個社會採取公平正義的結構,讓自由與團結成為可能…。
它不斷召喚我們與(心理上和社會的)不自由的惡性結構對抗,並在每個時代產生一個更符合福音視野的新藍圖,提醒我們時時秉持為愛與正義而付諸行動之創造力。
當我們生活在人類歷史的過程及視野時,「天國」提供給我們一項禮物、同時也賦予我們一個挑戰:「耶穌面對新社會的觀察角度及視野」時時擺在我們面前,成為我們的借鏡,並且邀請我們不斷地去革新。[3]

有份亞洲神學文獻說道:
「因此,天主的國普遍地存在與運行著。當人們面對那超越性的神聖奧秘時開放自己,以愛心為出發點走出自己、面向人類,為他人服務,天主的國就在工作…這正說明了天主的國度就臨在普遍的現實中,它遠遠超越了教會的界限與框架。
這是耶穌基督救贖工程的現實,也是基督徒和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救恩;這所謂的基本『神祕合一性』,深刻地把全人類團結在一起,遠遠超過那使人類分離的個別宗教。」[4]
2. 從福傳使命至對話(From Mission to Dia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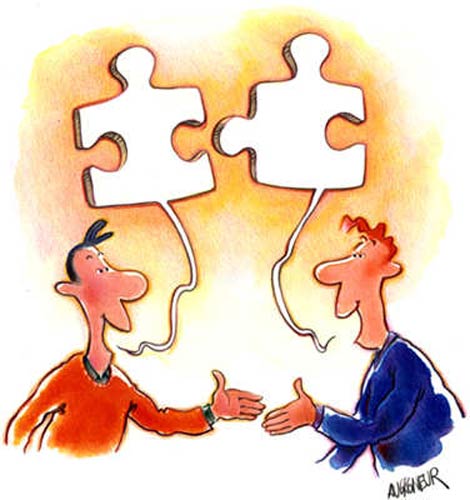
然而,除非文化和宗教結構有所改變,否則作為經濟和社會政治結構轉型要素的正義、是無法有效地推進的。要達到這種結構上的轉變、只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天主所賜予的自由,而這自由存在並活躍於所有民族的文化與宗教中,同時我們面對的也是回應天主召叫的自由人。
因此,對話無論如何成了福傳使命的重要途徑,對話不僅是雙方相互的理解及關係,也是讓雙方轉變與改造之挑戰和可能性。
宗教對話著重於文化以及宗教的轉化,這兩方面的轉化也是轉變社會的重要因素與方式。對話能促進社會的內部合作,並改進該社會的內在本質。不同的宗教團體可以透過對話來尋求共同的靈修經驗和社會價值(共識),同時也依據各自的宗教使命、動機、與靈修基礎,來積極促進和發展此共識。
在這種合作的過程中,也不排除宗教層面之間的對話、互動、和轉變。我們應多鼓勵此種對話與合作;甚至創造出從一個宗教轉換到另一宗教的空間。這樣看來,福傳成了具備對話使命的任務,因此,即便是在多元宗教以及充滿差異的某個社會中,不同的宗教也可以相輔相成、和平共存。
眾所周知,今日宗教之間的差異已日趨激烈,此現象甚至已導致暴力的發生。即使社會暴力現象的直接因素很多時候可能來自經濟及政治,但無可否認的是:宗教往往也是這些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還將暴力合理化。如此看來,激進主義足以使宗教本身成為暴力的替代品。
因此,宗教與宗教之間的交談和對話,當務之急就是需要從解決衝突和促進和好開始,繼續努力合作和尋求宗教之間的相遇經驗,透過這些經驗,各個宗教信徒才可以在天主面前深刻地與對方溝通與交流。
3. 從支配(操縱)到服務(From Domination to Service)

傳統上,傳教士不僅宣講福音,同時也教導信友如何回應福音,在這過程中傳教士會加入自己的文化、制度、禮儀、神學、和靈修方式。這些方式在某些部分也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傳教士往往以為自己的信仰與文化就是唯一的規範及標準。今天我們教會的官方不也仍然持守著這樣的立場嗎?
另一方面,大多數的信徒都會認為,福音必須降生在每一個文化中。耶穌道成肉身的典範本身就已證明了所有的(個人或社會的)轉變、都必須來自內在。福音會改變人,這種改變顯然是來自聆聽福音的人,而非福音的宣講者,這似乎是淺顯易懂的道理。
但是,今日教友很少有這種自由,「富有創意」的自由。教會應該是天國的僕人,也就是以「服務」為使命,而服務的首要態度便是空虛自己!但事實上很多時候並非如此。
看看大國統治小國的殖民時代,「統治」的概念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亞洲的教會幾乎都是隨著殖民者成了殖民地,「統治」或「操縱」的理念對當地教會來說不但不陌生,而且還相當自然!
今天有越來越多的本地教會興起了自主性和本土化的意識。1979年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國際福傳使命大會中,亞洲教會首先強調在自己的傳教區內具有自己的獨特使命及責任,同時對其他傳教區有共同的責任。
因此,傳教士的到來、並不是來主導一切,而是來協助與服務本地教會,共同促進福音和本地人民及文化之間的相遇。當相遇發生時,地方教會也因此而益加豐富。無可否認,梵二以後的教會觀是要使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能完整的共融,沒有任何一個教會可以稱自己是特權和典範。
4. 從出世(神聖)到入世(世俗)(From the Sacred to Secular)

福音清楚告訴我們要關注窮人、為窮人服務,才是表達基督信仰的重要任務。但相反的,那個時代很多傳教士普遍上反而受不少生活在貧困環境的信友的照顧及愛戴。
「梵二」之前,濟弱扶貧只是被視為福傳使命的結果或準備,直到「梵二」前後時期,為窮人服務才被視為是一種間接的福傳。
直到1971年的世界主教會議特別以正義為討論議題時,認為「正義」是福傳的整體幅度。那個時代在拉丁美洲也正發展出解放神學,而它很快地在許多貧窮的非洲和亞洲地區引起熱烈的迴響。耶穌會第32屆大會也特別指出「實踐公義的信仰」,認為促進正義才是表達信仰的具體行動。
如今福傳的首要趨勢和使命應該是「優先關懷窮人、為窮人服務」。事實上很多時候窮人是在困苦的生活中自助、自立、自強的。他們時時在為正義與公平努力奮鬥。所以不管任何一個宗教,只要它可以幫助窮人,並致力於正義,此宗教就應當被尊重與接受。因為它能貼近社會邊緣弱勢者的需要。
我們說福傳使命的「風格」,應該從出世(神聖化)轉移到入世(世俗化)。如今當我們提到宗教交談與對話時,其重點已不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攜手合作,能為社會做些什麼。
當然,狹隘的宗教交談仍有存在的必要,我們也可以將之保留給專家們。但對於一般的信友而言,宗教對話應該就是捍衛共同的人性和基本精神價值,為此而努力合作。我們在此面臨同樣的境遇,就是窮人必須捍衛自己的權利,要為正義而奮鬥。因而必須實際地走入人最基本的需要,並具體地給予協助。
窮人不會對各宗教為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感到興趣。一個神聖的宗教儀式應該是在精神上幫助、及給予貧困弱勢族群力量,鼓勵他們繼續為生活奮鬥。這就是所謂的轉變/轉化(transformation),也就是從神聖到世俗。

5. 從統一到和諧(From Unity to Harmony)

正是根據此概念及幅度,包括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99年在印度新德里公布的《教會在亞洲》勸諭中,也聲稱全亞洲可能在第三個千年會皈依基督。教宗提到,歐洲在第一世紀皈依基督,美洲人民在第二世紀都成了基督徒,所以第三個千年應該是輪到亞洲的時候了。
不曉得當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根據什麼理由或記號來做此推測。很多時候,教會習慣用「圓滿」的語言表達方式,認為其他宗教只能在天主教會內才達成圓滿。
當然,我們並不知道所謂的「圓滿」將會是什麼樣子。無疑地,這意味著(西方)教會很多時候是帶著階級色彩的分層圖像、以及自我優越的思想、來看其他宗教:「從局部到完整」;「從不完美到完美的圖像」。
然而,亞洲人是生活在一個多元種族、文化、及宗教的社會。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充滿著豐富性與多樣性的傳統,都是以「和諧」為標的,同時以「和諧」來維繫的。
「和諧」也意味著「多元」。「多元」不是「雜亂」;這不是一個沒有秩序的多元性,而是可以通過彼此對話、彼此豐富、及相互學習借鏡的一體多元的文化。

不同宗教之間的合作目的就是追求共同的目標。多元化在亞洲被認為是「豐富的」、而非「紊亂」、更不是「問題」。正如梵二大公會議曾表示,天主是全人類的共同起源和目標,由於人類都朝著這個目標前行,人在不同的宗教中體驗到大家都是同修者,是這同一條道路上同行的朝聖者。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撒旦(邪惡)與錢財(金錢的力量)。面對共同的敵人,不同的信仰者當然是把彼此看作盟友而非敵人。
每一種宗教應該彼此肯定他們對神的具體經驗,而不是判斷其他宗教先驗的神。彼此藉著尊重與聽取他人的經驗、來與其他宗教進行互動。
各宗教間的地平線將保持著對神的視野。異中求同是宗教的素養,當然任何倉促的宗教整合也是必須避免的,彼此的差異性是事實,是必須被尊重。尊重是和諧的條件,少了尊重就很容易掉入制式統一的迷思。
亞洲尤其在印度,「非二元」的概念更是加強了宗教間之和諧。這和諧表現在人與自然、物質與精神、人性與神聖之融合。這種和諧也可以在中國傳統對「陰」與「陽」的動態中運行。
印度一些神學家曾針對這福傳典範轉移做過以下論述:
「創造本身就是造物主的自我溝通,這溝通透過聖言與聖神、以各種方式,在不同的時間、透過不同的宗教,深入到所有人類。此進行式「神─人」相遇是救贖性的。然而,神的救贖計畫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靈魂,也顧及到天上和地上的萬物。
天主在古今中外藉著各個聖人和先知來實現此救贖。道成肉身的耶穌,是此救贖計畫歷史中的具體角色。但耶穌的使命亦是服務天主的使命,耶穌的使命並非取代天主的使命。耶穌以空虛自己的形式,與天主在其他宗教的自我彰顯合作,共同走向末世的圓滿。」[5]
我們可以藉著這樣的神學背景,提出三個關鍵問題:
1)、信仰與生命

今天當人們談論「正義」和「人權」時,事實上並不一定需要在任何宗教中尋求理由。正義與人權的需求來自超越宗教的「通俗」共識。社會中受壓迫的一群人、很多時候都遵循著這樣的意念與目標,而這些人的信仰往往是歸屬於多元宗教、多元派別的。宗教的差異對他們尋求正義與人權而言,並沒有多大關係。
基督徒常常會迫不及待地證明這些以正義和人權的生活目標是屬於耶穌的教導,但別忘了其他宗教的信徒也同樣可以其他的論據證明。
事實上人類信仰的經驗可以是大於基督信仰的,人們是在通往美好生活的路途中鎖定共同目標、尋求一種共識。
信仰與生活之間肯定有一種連結,但另方面似乎卻有著一定的模糊性,換言之,不知道是信仰服從生命,還是生命服從信仰。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把信仰的經驗與存在於其他宗教的信仰經驗,甚至非宗教的世俗意識形態做比較。這些比較可能會使我們意識到:信仰的作用也有可能是很有限的。
這現象是顯著的,古往今來人類如何敘述他們的生命故事,人們往往是在生活當中遇到問題時,才開始去反思「信仰」和「生活」之間的關係。這就像說話能力,當人遇到問題時、在急迫的時候就自然而然會想辦法,開口發問。
同樣,我們的信仰是植根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耶穌那平易近人的教導,而非植根於系統的神學或教會的制式訓導。「生命」是富有意義和可以詮釋的,「生命」才是「信仰」首當其衝的議題。信仰提供一種境界,讓生命發掘與開拓更多更深的意涵。
2)、信仰與社會

堅持激進主義的族群則拒絕這樣的區分,因此衍生出宗教的暴力行為。然而,這樣的區分對一個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會而言,似乎是有必要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個多元社會的生活方式就是「對話」與「合作」。除非某一方(如:傳統、文化、宗教或意識形態)放棄堅持自己的獨特性和優越感,否則對話是不可能發生的。
「對話」的前提是尊重各個領域的平等地位,包括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某群體以及包括任何一個宗教團體的信念及理念。屬於同一宗教的信徒,可以同時屬於不同意識形態的社群;譬如教友可以加入不同的政黨。這意味著、也強調「信仰」與「意識形態、宗教團體以及社會」之間的區隔。
在現代社會中,事實顯示人們選擇「不歸屬特定宗教團體」的趨勢是越來越高的。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及捍衛自己的自由意志。這揭示了「對話」是現代俗世生活一種必要的方式。當個體獨立性越強烈時,就非常需要藉溝通與對話來達至共識與合作。擴大來看,宗教團體的獨立性和私有化,也反映了教會(宗教機構)和國家政治應該區隔分明。
理論上宗教領袖不應該參與狹義的政治(參政)。很多時候政治活動和民間社會活動之間的區別總不那麼清楚。但是,宗教機構,有必要清楚及敏感於兩者的區別,宗教應該只參與民間的社會活動,而有必要與狹隘的政治保持一客觀的距離。
3)、信仰與教會

尋求「團結」及「平等」的教會團體,可以透過感恩聖事來表達與慶祝,並從聖事中汲取養分。如果教會內沒有這種活潑的信友團體,那這裡的聖事禮儀很可能會是很空洞的。
如今,教會越來越重視與堅持教友的自主性,同時也更注意到教會體制邊緣的團體。事實上,地方教會對自主權都有一定的需求與渴望。
教會的聖事禮儀生活本身並沒有什麼神奇的價值或力量,聖事其實就是信友以天主和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分享與慶祝的共同經驗。這裡值得一提「基督徒基本信仰團體」(基信團)給教會(信友)提供了一種信仰聚會的選擇;其實這種聚會形式是入世性的,因為它更貼近一般社會。教友透過這些聚會更能在多元宗教與多元思想的社會、去珍惜及捍衛自己的信仰。因而,他們比較不會陷入帶有政治色彩的極端主義。
結論:普世福傳使命

今天我們也該優先以同樣的語調來挑戰、尤其是那號稱自己為基督徒的富人、及有權勢的政治領袖。這些人正是在殖民時期剝削全球各地的窮人,在全球化的今天,他們仍繼續利用窮人來進行不公正的貿易。他們過度開發、濫用、及消耗地球資源,剝奪窮人生存的基本尊嚴與人權。這種現象屢見不鮮,無時無刻不斷在發生;這種現象會持續發生。
這種不公義的現象確實是件令人遺憾的事!因此,今天的福傳使命,首要關心的是:如何關注窮人,與窮人一起工作,尤其是要多關懷第三世界的人民。
一個關心「正義」的信仰不該只侷限於對窮人的關懷,它同時也應該把關心的焦點放在社會結構的改變上,讓受壓迫及受傷的社會可以得到改善。為達到此目的,教會需要與富人或當權者對話。
誰該對有錢人和那些剝削窮人的不正義主謀發出「先知性的聲音」?很多時候人們要求「富人為窮人祈禱」、「要求富人多多理解」、「要求富人給予關懷」、也「請求富人施予援助」。只有少數會跟富人提到「正義」的議題,勇敢地向富人索取賠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這表明了窮人是多麼的「認命」,他們只能選擇向貧窮的命運低頭。
在第一世界已開發國家的教會看起來更關心個人的道德行為,行有餘的才會注意公共與社會正義的議題。呼籲正義的先知性聲音應該時時迴盪在世界國際組織裡,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的等國際機構。這樣,福傳才能稱為普世性的使命。
世界各角落的窮人需要得到保護與協助。富豪與權貴的良心需要被喚醒及改變。也許在第三世界做福傳工作的先知性心聲、可以讓第一世界的福傳工作者聽見,以期那些生活在第一世界的富豪與權貴的良心可以被喚醒,並有所改變。
教會的焦點應該從教會的機構、教義、及禮儀,轉移到活生生的百姓生活和社會。這該由每一地方教會自動自發去實踐,並以完全屬於本地的需求與自主,來平等地與另一地方教會一起努力及合作。
教會必須保持對話與合作的態度。別忘了,身為亞洲的教會,我們必須有能力與其他宗教攜手合作、結成聯盟,來促進正義與和平的世界。這種宗教之間的互動、可以讓宗教團體本身和社會脫離激進主義與暴力。
這樣做,也正是在為天主「更新一切事物」(參默廿一5 )的使命鋪平道路。
(原文:〈New Images of Mission〉作者: Michael Amaladoss, SJ)
(特別感謝作者允許使用及摘譯此文章)
(特別感謝作者允許使用及摘譯此文章)
-----------------------------------------------------
後記:

基督信仰應該超越教會的束縛與藩籬,讓福傳的使命得以更自由、更自然、更活潑、更創意地適應每個環境。人除非重生,否則無法見到天主的國(參若三3)。耶穌很清楚表示人是需要不斷改變,不斷改變才能看見天國各種風貌及豐富的生命!基督徒的福傳使命首先就是認識自己和認識所身處的環境,時時調整及改變與他人的互動與對話方式。換句話說,福傳「使命」的面貌本來就因地而異。
連綴著土地與基督信仰養分的需求與供應,我們確切關心福傳的「使命力」與「翻轉力」,這是我們真實信仰的生命力!如何讓這生命力不斷流動於亞洲的社會?它不該只是瞬間的美感,而是細水長流的能量與美麗律動!
[1] 參 “My Pilgrimage in Miss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31, 2007.
[2] 《公教報》2010年12月12日,第3486期:「靈修研討會講者指出:依納爵靈修有助教會職務」
[3] George Soares-Prabhu, “The Kingdom of God: Jesus’ Vision of a New Society,” D.S.Amalorpavadass (ed), The Indian Church in the Struggle for a New Society (Bangalore: NBCLC, 1981), pp. 600, 601, 607.
[4]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Vol II, p.200
[5] Thomas Malipurathu and L. Stanislaus (eds), A Vision of Miss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Mumbai: St. Paul’s, 2001, p. 203.
Mumbai: St. Paul’s, 2001, p. 203.

